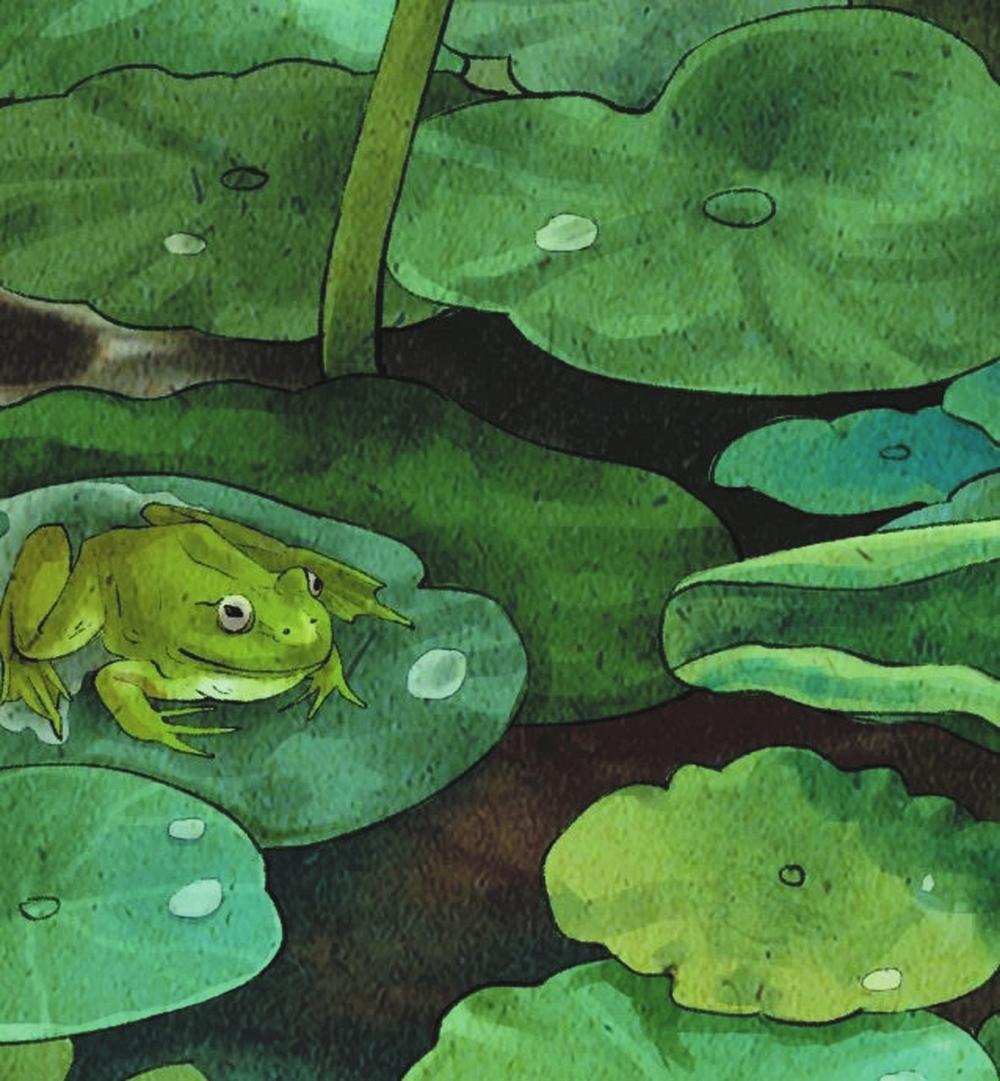黄孔曜
故乡夏夜,蛙鸣是绕不开的夜曲,而母亲的身影,总在蛙鸣里愈发清晰。暮色刚合,暑气未消,西天最后一抹橘红还恋着山尖,蛙群便已在池塘、田埂边按捺不住地“鼓噪”起来,似要把积攒了一整天的活力,全倾泻进这漫漫长夜。空气里还飘着白日晒过的泥土味道,混着稻禾的青涩,与蛙鸣缠在一起,酿出独属故乡夏夜的味道。
儿时,我总爱搬着竹椅,到院角那棵老柿子树下听蛙鸣。母亲会放下手中针线,那针线筐里还躺着未绣完的枕套,绣着半朵荷花,针脚细密。而后她摇着蒲扇,扇面上的牡丹在昏暗中若隐隐现,讲起“蛙儿守田,保稻丰年”的故事。她的声音轻轻的,和着蛙鸣,像月光漫过水面,温柔地漫过我的耳畔。
蛙鸣起时,先是零星几声,像谁用指尖轻叩瓦罐,“呱”一声,又停了,隔几秒,另一处再应一声,带着几分试探。“呱呱”“咕咕”,蛙鸣高高低低,层层叠叠,把夜色织成张会响的网。塘里荷叶上的蛙嗓门最亮,胸腔鼓得老高,像是领唱的将军,昂首挺胸地指挥着田埂边“士兵”应和,连远处溪沟里的小蛙也挤着声儿,细弱却执着,要掺进这热闹。母亲就着蛙鸣教我认星,哪颗是牛郎,哪颗是织女,说他们隔着银河,就像塘里的蛙和溪沟的蛙,虽隔得远,叫声却能凑到一块儿。蛙声成了星空下最生动的背景音,偶尔有流星划过,拖着银亮的尾,母亲会笑着说:“是蛙儿的歌声,把星星都引来听啦。”我便拍着手,看流星坠入蛙鸣里,恍惚觉得整个夏夜都在和我们嬉戏,连老柿子树的叶子也跟着笑。
想捉蛙时,我和伙伴们备上竹篓、手电。竹篓是父亲编的,竹篾间还留着淡淡的竹香,手电是装两节大电池的那种,开关一按,光柱能射得老远。母亲在廊下望着,廊檐下的马灯亮着,把她的影子投在地上,忽长忽短。她叮嘱:“别摔着,别伤着蛙。”声音被蛙鸣托着,传到田埂边。手电光束扫过,便能瞅见塘边鼓着腮帮子的“主唱”,绿莹莹的背在光下泛着光,可刚要伸手,蛙“扑通”跳进水里,只剩一圈圈涟漪和手电光里晃荡的水草,水草上还挂着水珠,亮晶晶的。偶尔逮着只蛙,就装在篓里,它“咕咕”抗议,小爪子在竹篓里扒拉着。母亲便笑着接过篓,指尖划过竹篾说:“蛙儿想回家啦,它的家人还在等它唱歌呢。”最后,我总在母亲嗔怪里,看蛙重新融入蛙鸣大合唱,它一入水,便立刻“呱呱”两声,像是在跟同伴报平安。
有一回,暴雨突至,天空转眼就被乌云压得低低的,蛙鸣被雨点击碎,成了断断续续的碎片。我慌得要往屋里跑,脚下的泥地已经开始发滑。母亲却拉我蹲下,她的手刚从水里捞过衣服,带着湿漉漉的凉意,说:“听听雨里的蛙鸣。”雨砸在荷叶上,“噼里啪啦”像无数个小鼓在敲,蛙声反倒更脆了,“呱呱”“咕咕”一声比一声响亮,像在和雨较劲,谁也不肯认输。母亲的裤脚浸了水,紧紧贴在脚踝上,凉风吹过,她打了个轻颤,却仍紧紧攥着我的手,说:“别怕,蛙儿都没跑,它们在给雨伴奏呢,咱也听听雨的故事。”那夜,雨幕里的蛙鸣,成了我心里最勇敢的歌,母亲的体温,是最暖的依靠,比身上那件被雨打湿一半的小褂子暖得多。
后来,我上了学,白天要去学堂,晚上便少有时间再去柿子树下听蛙鸣。我写字的笔尖在纸上划过,“沙沙”声和着窗外的蛙鸣,倒也成了一种别样的和谐。她会坐在旁边,借着灯光缝补我的衣服,针穿过布面的“刺啦”声,也融进了蛙鸣里。有时,我写着写着睡着了,醒来时身上盖着母亲的薄毯,桌上的绿豆汤还温着,窗外的蛙鸣依旧热闹,像在为我唱摇篮曲。
如今,城市灯火亮堂,高楼一栋接着一栋,把天空切割成一块一块的,蛙鸣成了记忆里的潮声,偶尔在梦里响起,却总隔着一层模糊的纱。但午夜梦回,那些“呱呱”声,仍会漫过岁月,把故乡的夏夜,鲜活地铺在眼前——老柿子树影摇晃,树影里有我和伙伴们追逐的身影;母亲蒲扇轻拍,扇面上的牡丹好像还在动;蛙鸣裹着稻香,漫过田埂,田埂上还有我和母亲踩过的脚印;漫过童年,童年里有绿豆汤的甜、有母亲的笑;漫进永远温热的乡愁里。